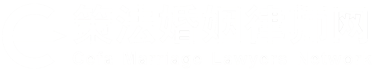婚姻和感情是两个领域,法律调整的是婚姻关系而不是男女感情。今天的心爱之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审美疲劳,明天可能会变得冷漠甚至咬牙切齿。理性法则如何控制千变万化的情绪?感情没了,婚姻解体。至少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保障。也许“婚姻契约”是聪明女人的明智选择。深圳婚姻律师来回答一下有关的情况。

著名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表达了一种流行的契约婚姻观:“爱是为了爱,财产是为了财产。”爱与财产的分离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的。但是在爱情和非此即彼之间的选择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极端例外,大多数婚姻都处于这两者之间:爱情可能已经褪色,财产可能没有分割,婚姻可能没有破裂。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家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从而成为一种稳定的正常生活。家庭关系到个人幸福和文明修养。它具有育儿、塑造人格、培养社会公德、养成良好风俗习惯等社会功能。因此,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会认为家庭具有独立性和高于爱的价值,家庭稳定已成为立法者的首要任务。
家庭财产制的衰落:个人财产制和清晰的不动产。家庭社会稳定发展首先需要依赖于“家庭教育共有财产”这种物质性纽带。革命根据地时期激进的婚姻制度立法工作虽然可以肯定了离婚自由主义原则,但“同财共居”的家产制传统却一直没有保留下来。例如,与土地管理有关的财产法就延续了古代家产制。
无论“打土豪分田地”还是教学改革创新开放政策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财产法的主体作用不是我们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资源不会出现因为他们结婚或离婚而立即发生一些法律变更。家庭贫困人口的不断增长变动情况导致整个村庄要经过这样一段学习时间问题之后能够重新在家庭环境之间信息进行“调地”。
同样,与土地利用相关的宅基地划分方法也是学生按照自己家庭来进行的,离婚不可能直接导致农村宅基地的分割。城市的房屋产权保护虽然我国登记在家庭内部成员一方的名下,但在法律上也属于不同家庭共有财产,以至于房屋购买服务合同内容要求夫妻关系双方签字。
1950年《婚姻法》中确立的夫妻共有财产制就源于“中国人的理想是家庭主要成员模模糊糊地共同努力拥有家产”的法律研究传统。而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中,甚至已经明确规定将个人财产吸纳到家庭财产中。至于在继承法中,虽然法律上赋予了女儿与儿子平等的继承权,可实际上女儿基本上不继承家产,强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依然遵循着“同居共财”的逻辑。
新中国原婚姻法表面上激进,但其对共同财产的重视是保守的。再加上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以调解为基础”的司法政策,中国的家庭稳定并未受到根本影响。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促进了个人欲望的膨胀,文化左翼的后现代思潮消解了传统价值观。

“单身婚”“契约婚”“ AA婚”以及同性恋婚姻已成为中国家庭生活乃至时尚人士追求的一种价值选择。在此背景下,立法和司法解释不断打破“家庭财产制”,维护家庭财产关系的稳定。2001年,全国人大对婚姻法进行了全面修改,明确划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所有财产”。
同时,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人民中华民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i)(即司法解释i)特别强调,个人财产不能通过婚姻转化为共同财产,导致了“婚前财产登记”的浪潮。在财产平衡、人身自由和家庭稳定首次有利于人身自由方向的情况下,后来最高人民法院以破坏家庭共同财产为契机解释了《婚姻法》,家庭财产制度的衰落意味着家庭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开始动摇。
对家产制的摧毁中,最大力量就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离婚房产分割的具体规定。对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家产中最大的财产就是房屋。房屋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家庭生活必须拥有的居住空间;它不仅是属于财产权范畴,而且体现了人类最低限的生存权。
如果说婚姻奠定家庭的精神基础,那么房产就奠定了家庭的物质基础。“家”不仅是一种血缘伦理关系,而且是一种对房屋开辟的物理空间的占有关系。由此,对于注重家庭价值的中国人而言,房产往往与“家”联系在一起,在生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

深圳婚姻律师发现,在家产制中,最主要的家产就是土地与房屋。以家庭为主体的土地承包制度不断受到“土地私有化”主张的冲击,而房屋家产制的瓦解,则是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开始的。